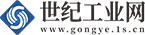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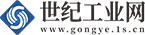
1804年,江户诗人大田南亩(1749-1823)因公务赴长崎驻留,在此期间的某日他访问了唐馆。唐馆又称“清馆”,日文称“唐人屋敷”,乃是赴日清人的居留之处,其地位类似于广东十三行或是釜山的草梁倭馆。访问唐馆之后,南亩留下了如下诗句。
天后土神关帝祠,几番船主赛长崎。门联匾额多相似,疑入苏州桂海涯。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图一 长崎版画《唐人屋敷景》,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唐馆占地九千余坪(一坪为六尺平方,约3.3平方米),里面有数座祭祀华人神灵的庙宇,自然都是中国风格的建筑。而热心于祭神仪式的人物,则是那些每年奔波于江南和日本之间的清朝船主。再加上华人手书的各类门联匾额,都让诗人觉得自己恍如身在苏州城(图一)。南亩诗中抒发的感叹,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苏州在十八到十九 世纪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当时的苏州之所以重要,自然与这一时期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密切相关。清朝官府为了采购铸钱用铜材,每年都要派遣商船赴长崎。其管理机构被称为“官铜局”,有官局和民局之分,而其中的官局即开设于阊门外的桐泾里。那些乘船赴日并负责交易的所谓办铜商人,有船主、副船主、财副等具体分工,他们当中自然也以苏州人为最多。因此在清代中期的百余年间,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可以说有很大部分实际上是在苏州与长崎之间展开的。
然而关于这段时间两国交流的具体情形,实际上不明之处尚多。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始记录未能逃过太平天国的战火,如何收集和整理保留在日本的各类史料和记录,遂成为无法绕过的重要课题。笔者近年来专注于此,在日本各地的调查过程中时有一些意外收获。本文要介绍的,便是2019年夏天在东京某藏家处看到的一封清人书札。
图二 姜跃泉致木下逸云书札
这封书札只有一纸,长23.5厘米,宽13.0厘米,是清代的常见样式。虽因虫蚀略有破损,但全文基本清晰可辨。这里先解读原文如下(图二):
捧诵瑶函,并蒙厚惠。拜领之余,无以奉报。聊具朱砂印色壹两、线胶壹匣、艾绒壹匣、朱膘壹包,藉供文玩之需。外所要办洋紅、铅粉脂膏,附便寄去,该价已向秋涛先生处算明矣。将来如要各种颜料,其价即询秋涛先生可也。草此布候,文祉不尽。跃泉姜应龙顿首。十一月初二日。
这封信函的发信人名为姜应龙,“跃泉”当为他的字或者别号。从引文可知,他委托名为“秋涛先生”的人带去收信人订购的颜料若干,其中包括十分贵重的洋红(carmine,原料为产于中南美洲的胭脂虫)。同时他还另外附赠若干与 “文玩之需”相关的商品,多为治印必需之物。说是馈赠,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寄送免费试用品。因为在信的最后,发信人还承诺通过秋涛先生继续为收信人提供各种颜料。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不妨说这是我国早期的海外代购记录,或是最早也未可知。
图三 姜跃泉书札封筒正面
信中的“秋涛先生”,正是一名协办官铜的苏州商人。其本名叫王秋潭,秋涛是他的字或别号。从《割符留账》等日本方面的贸易史料中,我们可以找到他的四次长崎入港记录,分别是日本天保七年(1836)作为申七番船财副、天保十二年(1841)作为丑五番船财副、天保十四年(1843)作为卯六番船副船主、弘化四年(1847)作为未一番船副船主。当然,这些仅仅是他的部分渡航记录,因为如果担任财副以下的职务,或是以普通船客的身份赴日,则名字不会记入《割符留账》。另外,王氏家族为官商,秋涛之弟即王元珍(?-1860,号梅庵)担任过总商,乃是统领官铜局的负责人。元珍坐镇国内,而秋涛作为其代理人奔波于苏州与长崎之间。后者留传至今的书札有三十余通,其中可以看到他把姜思序堂的绘画颜料输出日本的记录,这里无暇一一列举。因此书札作者姜应龙,笔者断定为彼时的姜思序堂主人无疑。姜思序堂开张于明末,是苏州城内专门制造和销售绘画颜料的著名商号。晚清以后虽数易其主,但字号和制作技艺一直传承到今天。难得的是,这件信函的封筒(15.4厘米×6.8厘米)也完整保留至今。其正面记录了收件者姓名及附带物品,可以看到如下记载(图三):
内字、外颜料两包,拜祈王秋涛先生顺寄确交木下逸云先生查收,姜跃泉缄托。
收信人即木下逸云(1799-1866),与僧铁翁、三浦梧门并称“长崎三大画家”,是幕末时代日本南画界名重一时的人物。逸云年轻时曾入苏州人江稼圃(1746-1826)门下学画,同时与稼圃堂弟、著名船主江芸阁(1772-1837)也多有交往。稼圃与芸阁既是同族,又都是嗜好诗文书画的雅人。芸阁住在阊门外上塘街庞家衙内,距离阊门内东中市的姜思序堂不远。逸云虽然远在长崎,但通过江氏兄弟知道这家专为画家提供颜料的著名商号,也是很自然的事。至于说通过赴日清商订购颜料,对他而言也并非难事。
图四 姜跃泉书札封筒背面
另外,封筒背面的一行文字也值得关注,其文为“(壬)辰拾壹月初二日封寄”(图四)。可知此信的寄出时间,是在道光十二年(1832)冬。此时长崎文坛的一件大事,是书画会的举办。生活在同时代的画家蒋宝龄在其《墨林今话》(1852年刊)卷十八“日本宰官”条中记其事云:
日本国长崎木下相宰,字公宰,号逸云。书画俱法董思翁,兰竹石小品亦清逸有致。其绢素厚而密,似不用胶礬者。兼長笔札,其言云:长崎每岁春秋两度,设书画雅集之筵,四方名士咸会。有不至者,亦作书画彙投。彼国翰墨之盛可想见矣。
引文中的“书画雅集之筵”,指的是 1830年前后数年间由长崎清谭会主办的书画展览,当时称为“书画展观会”。展观会至少举办过八次,参与者不仅有日本国内各地的文人墨客,也有来自清朝、朝鲜、琉球诸国的文人,堪称是东亚地区最早的国际艺术展。逸云除了自己有画作参展,同时更以清谭会盟主的身份,主持了展观会的举办。因此不难想象,他的名声早已在苏杭一带文人圈中传播。甚至像蒋宝龄这样从未去过日本的江南文人,也注意到逸云的存在。而姜应龙作为一家苏州商号的主人,利用这个机会不失时机地发信至日本并慷慨赠送颜料,商业嗅觉堪称敏锐。书札中的短短数语,也把他希望拓展海外市场的雄心展露无遗。
有清一代中日两国之间的书画交流十分频繁,这是周知的事实。一般来说,书画家因有作品传世,其文化活动对后人而言属于可视的世界。至于在当中穿针引线的商人,在官方和民间的贸易史料中,也可以找到若干蛛丝马迹的证据。相比之下,经营绘画颜料的商家直接现身并留下记录,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之事。从这个意义来说,这封信件展示了后人难以看到的历史侧面,可谓弥足珍贵。
木下逸云的画作,以长崎历史博物馆收藏最多。他的画作中是否使用了包括洋红在内的姜思序堂制颜料?另外,在距离长崎不远的武雄市历史资料馆(佐贺县),收藏了当地领主岛锅茂义(1800-1862)从长崎购回的普鲁士蓝。据岛锅家的记录,这些普鲁士蓝于1830年左右进口自中国,因此当地称之为“唐口绀青”(日文称普鲁士蓝为绀青)。这是否也是来自姜思序堂的颜料?上述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唐权)
来源:姑苏晚报
关键词: